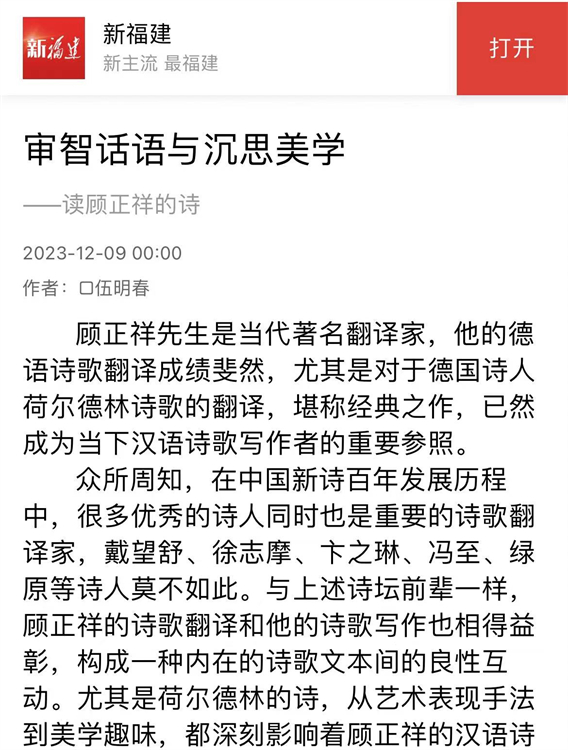
12月9日,新福建报道审智话语与沉思美学-读顾正翔的诗
原文转载如下:
顾正祥先生是当代著名翻译家,他的德语诗歌翻译成绩斐然,尤其是对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歌的翻译,堪称经典之作,已然成为当下汉语诗歌写作者的重要参照。
众所周知,在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历程中,很多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重要的诗歌翻译家,戴望舒、徐志摩、卞之琳、冯至、绿原等诗人莫不如此。与上述诗坛前辈一样,顾正祥的诗歌翻译和他的诗歌写作也相得益彰,构成一种内在的诗歌文本间的良性互动。尤其是荷尔德林的诗,从艺术表现手法到美学趣味,都深刻影响着顾正祥的汉语诗歌写作。阅读顾正祥的诗,笔者不禁联想到爱尔兰现代诗人叶芝的一首著名的短诗《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叶芝在这首诗里所着力勾勒的“青春”和“真理”之间微妙的张力关系,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突出的智性品格。在顾正祥近年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种智性品格在语言、主题、形式等方面的多元化艺术表现。
与年轻诗人热衷于抒写风花雪月的情感不同,顾正祥的诗更多的是表现一位历经时代风云变化的成熟知识分子关于世界、人生、艺术的深切体验和独特感悟。他的诗大多采用审智话语而非传统的抒情话语,往往呈现某种突出的沉思美学品格。这些诗作既体现了宏阔的想象视野,又具有深邃的诗思。譬如,诗人以乌云作为自我形象的参照物,表达了一种堪称沉稳而深邃的人生况味,他在《我羡乌云》一诗里这样写道:“我羡乌云/浓浓的乌云/你虽面目可憎/但有你的衬托/蓝天才更妩媚/人生才够回味/我亲乌云/浓浓的乌云/有你的一往情深/大地才不干渴/江河才起波涛/山岭才变苍翠/我敬乌云/浓浓的乌云/多亏你疾恶如仇/以横扫千军之势/涤荡人间污秽/迎来万丈春晖”,从“羡”到“亲”,再到“敬”,几个动词的微妙变化不仅体现了诗歌情境的起承转合关系,也暗示了写作主体对于“乌云”这一核心意象认识的不断深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这首诗取了一个副标题“我的美学观”,由此不难窥见作者在这里试图建构一种关于人生、自然和世界的“乌云美学”观:“乌云”并非一个自外于人生、自然和世界的独立存在,而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具有丰富内蕴的组成部分。
而在另一首诗《我是一个乞丐》里,作者别出心裁,通篇以“乞丐”自比,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历经艰难困苦、勤学进取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第二节的表述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我是个执拗的乞丐/乞讨不分天气/无论阳光灿烂/还是狂风呼啸/都要向互联网乞讨”,面对我们所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位清醒、自觉的资深知识分子不甘人后,仍在不断地求索、思考着,并且用现代诗歌的方式作出诗性的反应。这种求索、思考的积极姿态一扫“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暮气,而是显得十分自信而从容。这种自信和从容的抒情姿态,在顾正祥的其他作品也多有呼应:“既是‘前辈’,莫滋生/白发和夕阳的哀悲/或许能用你的余热/为后人竖一座丰碑”(《“前辈”小议》)、“如今已届老年/问我有何期待/我成了变相的富翁/虽囊中羞涩/似有金山银山”(《如今已届老年》),这里所说的“丰碑”“金山银山”,不正是叶芝《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一诗里所说的“真理”的诗性化身吗?
自从移居海外之后,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显然也是顾正祥在诗歌写作过程需要直面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位深谙中德两国文化的诗人,顾正祥以一种成熟、理性的方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在《别喊我“老外”》一诗里道出了诚挚的心声:“别喊我‘老外’/我爱内卡河畔的图宾根/像爱扬子江边的大上海/别喊我‘老外’/我在图宾根穿街走巷/好似在紫禁城里徘徊/别喊我‘老外’/歌德席勒荷尔德林/和李白杜甫白居易/同是我的所爱/别喊我‘老外’/德意志和龙的传人/在我身上汇成/同一个血脉”,不难发现,诗中列举的一系列中德文化符号,一方面突出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另一方面也充分流露出作者努力沟通、融汇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执着努力和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今晚为何相聚》一诗里同样强烈:“于是/就在这大厅/我斗胆想象/大西洋问候太平洋/内卡河拥抱扬子江/中华古国和德意志/同是养育我的爹娘/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皆是我驰骋的疆场”,在这里,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良性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想象的图景,更是像顾正祥这样脚踏实地的践行者以诗歌翻译、诗歌创作等方式不断探索、不断拓展的话语空间。顾正祥曾这样阐释他的诗歌翻译理念:“试图在跨越德中两种语言的鸿沟之后,让它们脱胎换骨,在另一语境中获得诗意的新生:既最大限度地反映原诗的内涵、形象和韵味,又企望在转化为目的语后也能出神入化。”这个理念,在顾正祥那里,恐怕不仅适用于德语诗歌的翻译,也适用于他的汉语诗歌创作中对于中外文化因素的融合贯通以及诗人文化身份的彰显。
总之,顾正祥的诗不仅为我们贡献了丰富的智性诗歌话语和较为突出的艺术形式探索,也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和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观照视角。